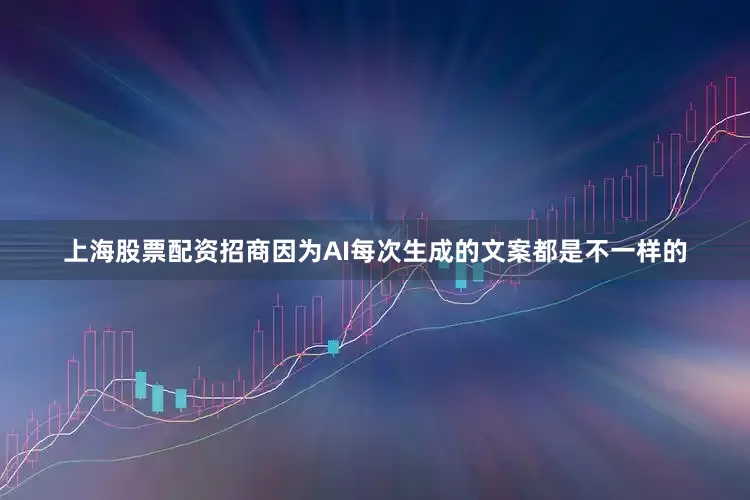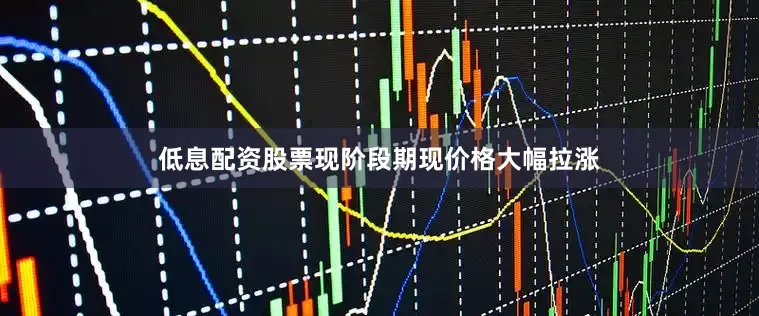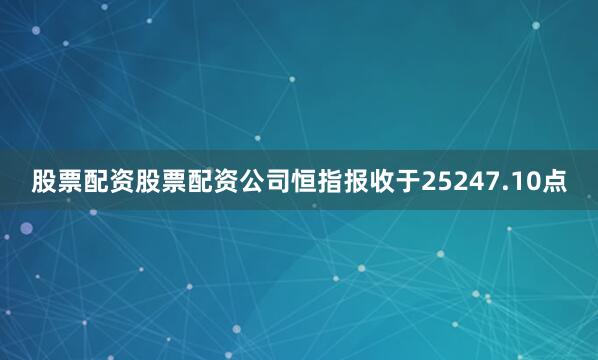秘书谈康生
——黄宗汉谈话琐忆
阎长贵
黄宗汉曾担任康生的秘书,伴随其左右长达十余载。在此期间,他亲身参与了康生主导撰写的针对苏共的“九评”文章,以及见证了康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康生离世后,鉴于他生前对黄宗汉的赏识,黄宗汉因此被委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之职,荣膺副军级待遇。
他与康生共事已久,对康生的性格与行事风格自是了如指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仅未能留下对康生的全面回忆,甚至在某个特定方面或问题的详细回顾也付之阙如。这种情况,既令人惋惜,又实在难以弥补和挽回。类似的情况,还有李鑫,他担任康生秘书的时间甚至更长,康生去世后,他成为了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据说,他还是首位向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然而,他比黄宗汉去世得更早,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康生的回忆材料。
显而易见,若缺乏李鑫与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我们全面(涵盖正面与负面)地认识和理解康生便会受到很大局限。遗憾的是,在李鑫和黄宗汉生前,竟无人进行相关资料的“抢救”工作,甚至无人提及此事,这实为一大遗憾,亦是一课教训。中华民族历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史学研究享誉全球,然而在当今时代,却有人竭力让人们忘却历史及其真相,这让人深感困惑。试问,我们现今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能否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相提并论呢?
《史记》问世已有两千余载,至今无人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常言,“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然而,若失去了“信史”的依托,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又如何能够向未来传递历史的智慧呢?
言归正传,关于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资料,虽然并未形成全面且系统的概述,然而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与黄宗汉及其他人士的交往中,他还是有所提及康生的一些事迹。纵使这些内容并不完整、不成体系,但对于深入理解康生这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国家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不敢自诩,撰写了这篇简短的文章。

一、
在1967年至1968年间,我有幸担任江青的秘书,期间结识了黄宗汉先生。我们同为小知识分子,且在负责人身边担任相似职务,因此相识后倍感亲切,宛如无话不谈的挚友。在“文革”这场风暴中,黄宗汉先生显得尤为幸运,他一直深受康生的器重。相较之下,我仅在江青身边工作了短短一年,便被她诬陷为“坐探”,不幸入狱,被监禁起来。
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地重逢相聚,畅谈旧事。他时常关切地询问我经济上是否遇到困难,并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我对此深怀感激。2001年3月22日,我与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同前往国防大学探望他(在康生被揭露和批判后,得益于某位大人物的关照,他仅被降至国防大学师职教员之位,而苏双碧先生与他同是福建人),在会面交谈中,他谈及了康生与中央某些人物的关系,我认为这些内容至关重要。归家后,我随即进行了追记,如今将其整理成文,公之于众。
1. 康生懵然不知,《五一六通知》中所提及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竟是指刘少奇。1966年,这段历史风云变幻的序幕缓缓拉开。在19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之际,康生竟与戚本禹、张春桥等众多人等相同,均未意识到《通知》中所指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正是刘少奇。
在本次会议的发言中,他还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自我检讨。他指出:“在王明路线时期,我确实犯下了错误。那时,职工国际发布了一份文件,指责少奇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也曾信以为真,对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中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并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反对他的文章,署名是谢康。”
此事非他人之过,纯属个人思想之误,未能认清少奇同志身处白区,却忠实地代表着毛主席的路线。”(引自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外,我在延安时曾向您作出检讨,今日依旧诚恳地向您道歉,并承诺未来仍将不断反思。决不能效仿某些人,他们在当时既反对您,又取代了您的位置,却未曾进行丝毫反省(总理插话:指的就是那位××啊!)

康 生
2. 康生与邓小平之间关系密切。据黄宗汉所述,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曾一度遭遇冷遇,而其重新崭露头角,主要得益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支持。进入60年代,邓小平与康生共同负责领导“反修”运动。
邓在文革中一方面,邓与康生关系亲密;另一方面,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康生担任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要职。(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期间的书籍中,对于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拜访各种人物的情况有详细记载,但关于拜访康生的事迹却几乎不见踪影。——笔者)
康生离世之际,他所获得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两顶荣誉,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评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及康生的错误,并强调其严重性,建议中央予以批判。然而,邓小平对此持不同意见。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其顾问团中便包括了李鑫(前文已提及,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有人企图对李鑫进行打压,但邓小平力保其地位,确保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不便,李鑫转任经济所副所长。
康生之所以犯下众多恶行,固然与其个人品质紧密相关,但是否也应从制度层面探寻其成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良好的制度能够遏制坏人肆意妄为。”——引述者
在此,笔者需补充一事实:自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委以林彪重任,主持政治局生活会并对刘少奇提出批评。然而,林彪与江青联手,将批判的重点转向了邓小平,甚至将他与敌对势力的矛盾提升至极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深感工作难以为继,于是提出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负责的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事务移交给“康老”——此举措或许也是邓与康之间良好关系的有力证明。
3.康生与周恩来关系甚笃。自康生病榻之上,周恩来屡次探望,提及他们同年同月而生(1898年),并回忆起在上海共事的时光(即“特科”时期),当时他们同属的仅余三人(周、康、陈云)。康生不幸先于周恩来离世,相差23日之短(1975年)。“请去到更需要您的地方去吧!”
4.“主席的意思是,江青成为政治局委员便足矣。”黄宗汉还提到,某夜,李讷敲他的门,称要找康老,想揭发江青的一些问题。笔者对此也补充一二。
七八年前,在撰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时,我曾记录了林彪、周恩来总理以及陈伯达等领导人对于江青的赞誉之词。然而,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康生对江青的赞许之语。此外,还有一则故事,是关锋亲口向我所述。
1967年2月1日在0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因打倒陶铸所采取的方式和程序——这一点,他特别予以强调——表示了批评。随后,他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会议自然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负责主持。
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有必要指出,相较于康生与陈伯达,江青对康生的态度显得更为尊重。我曾目睹江青以“三娘教子”般的严厉斥责陈伯达,却未曾见她对康生有此等态度。从周恩来总理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的称呼均为“江青同志”,而康生则常直接呼其名。这或许源于延安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推断康生对江青缺乏尊重(或者说,并不畏惧江青)。
康生在公开场合屡次提及江青同志,甚至在他写给江青的信件中,有时竟以“呈江青同志亲启”的字样落款。这种称呼上的转变,无疑值得我们深入观察与深思。
5. 不,所有文物都将上交国家。此外,他个人存款的8000元也决定不留给子女。
二、
于黄宗汉府上,我与苏双碧先生亦目睹一景。便是他家壁上,悬挂着数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依稀记得,其中包括叶飞、李德生、吴阶平等人的墨宝。这些作品的内容均是对黄宗汉先生的赞誉——遗憾的是,当时未曾详记其具体内容,至今亦难以回忆。
当时,我向黄宗汉询问这些文字的起源。他解答道: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康生执掌了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的大权,然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书写亦感吃力。尽管如此,某些事务仍需他作出表态或签署姓名。通常是我起草文件,康生随后签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解脱了部分人的困境,亦解决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部分人因感怀之情,挥毫泼墨以示谢意。而我,不过是借助他人的庇护,稍享清凉。此外,也有人出于友好之意而书写。情形大致如此。苏双碧先生与我一同赞叹道:“你此举实乃善举!”
2012年12月,北京东城沙滩
炒股配资10倍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