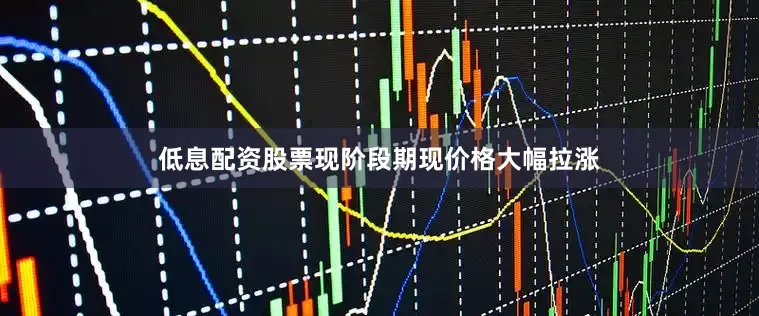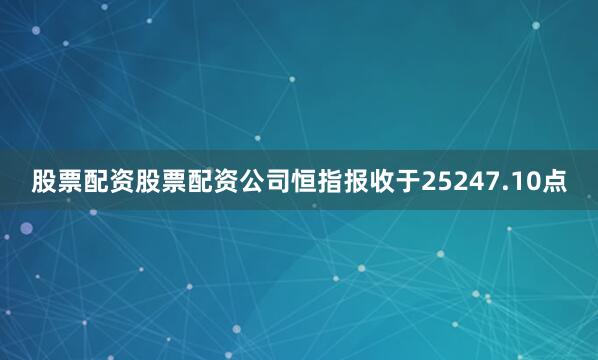宋美龄9岁被送美国,十年后归国,宋庆龄见她第一面就愣住了
1917年的上海码头,潮湿的江风裹挟着咸腥味,一个打扮时髦、身姿窈窕的年轻女子走下舷梯,眼神里带着一丝初来乍到的好奇与疏离。
她就是宋美龄,离家十年,终于回来了。前来迎接的二姐宋庆龄,看着眼前这个妹妹,一时间竟有些语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眼前的“小妹”满口流利的英文,带着浓浓的美国南方口音,穿着最流行的洋装,举手投足间,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名媛。
宋庆龄记忆里的那个穿着小旗袍、梳着辫子、跟在身后软软糯糯喊“姐姐”的小人儿,仿佛被彻底抽换了灵魂。
时间拨回到十一年前,1906年的宋家公馆,空气里都是樟木箱子和西洋香水混合的味道。
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穿着一身精致的小旗袍,正对着西洋相机镜头,努力地憋着笑,脸颊肉嘟嘟的,像个饱满的红苹果。
她就是9岁的宋美龄,宋家最小的女儿,全家人的心头肉。父亲宋耀如最疼她,亲昵地喊她“小灯笼”,因为她走到哪儿,哪儿就亮堂起来。
这个“小灯笼”可不是个文静的主儿,调皮捣蛋起来,几个哥哥都拿她没办法,但只要她一撒娇,整个宋家都得缴械投降。
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张照片拍完的第二年,宋耀如做了一个让所有亲戚都目瞪口呆的决定:把这个还没到十岁的宝贝疙瘩,送到美国去。
那年头,别说女孩子,就是男孩子出国留学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年纪,简直是闻所未闻。
但宋耀生来就是个“破局者”,他就是要让女儿们接受和儿子一样的、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早已先行一步。
于是,小小的宋美龄,带着对远方的懵懂和对家人的不舍,跟着二姐宋庆龄的朋友,踏上了去往美国的邮轮。
漫长的航行,海水是单调的蓝色,海鸥的叫声也带着孤单。她第一次体会到,原来离开家,是这样一种心被掏空的感觉。
到了美国,一切都是陌生的。高耸的建筑,金发碧眼的洋人,听不懂的语言,她像一株被移植的幼苗,惶恐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
她先是被送到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寄宿在一个叫波因德克斯特的家庭里。这家人对她很好,亲切地称呼她“珍贵的东方小东西”,但文化隔阂像一道无形的墙。

吃饭要用刀叉,说话要轻声细语,见到长辈要行屈膝礼,这些规矩让她浑身不自在。夜深人静时,她会偷偷躲在被子里,想念上海家里那碗热腾腾的阳春面。
寂寞是最好的老师。为了不被孤立,她开始发了疯一样地学英语。从一开始的结结巴巴,到后来能用带着佐治亚口音的英语和同学流利地辩论,她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她骨子里的那股子好胜心被彻底激发了。在学校里,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人照顾的“小灯笼”,而是一个成绩优异、才华出众的东方女孩。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她从著名的卫斯理安学院毕业时,她已经彻底融入了美国社会。她热爱莎士比亚,能弹一手好钢琴,熟悉西方礼仪,甚至思维方式都完全西化了。
她自己后来都承认:“我身上唯一像东方人的,大概只有这张脸了。”
所以,当她1917年回到上海,面对家人时,那种强烈的疏离感是双向的。她看家人觉得陌生,家人看她又何尝不是如此?
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她就闹了笑话。家里人习惯了用筷子,她却下意识地寻找刀叉,动作显得笨拙又滑稽。
更要命的是她的中文。十年不说,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日常交流磕磕巴巴,很多词都想不起来,只能用英文代替,急得满头大汗。
这让大姐宋霭龄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专门为她请了中文老师,从头开始补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那段时间,宋公馆里时常传出小妹背诵《论语》时,夹杂着英文单词的古怪腔调。
这种文化上的“夹生”状态,让她在回国初期的社交圈里显得格格不入。中国的名媛觉得她太“洋派”,不懂含蓄;而她又觉得上海的圈子太过拘谨,缺乏活力。
有一次,她陪母亲倪桂珍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堂会,按规矩女眷们要安静地坐在后排听戏。可宋美龄听得兴起,竟忘了形,直接站起来大声叫好,引得满堂侧目,让倪桂珍尴尬不已。
这件事让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隔阂有多深。她像一个有着中国面孔的“异乡人”,在自己的故土上,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接纳的“外国人”。
正是这段特殊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宋美龄独一无二的特质。她既有东方女性的坚韧,又有西方女性的独立与自信。这种东西方文化在她身上的奇妙融合,让她在日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拥有了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她可以毫无障碍地在美国国会用流利的英文发表演讲,为中国争取援助,那种优雅与自信,征服了无数美国政要。她也能穿上旗袍,以东方女性的温婉形象,团结国内各方力量。
可以说,从9岁那年踏上邮轮开始,宋美龄的人生就被设定成了一场漫长的“寻找身份”的旅程。她的一生,都在试图弥合那个上海“小灯笼”与美国毕业生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内在的撕裂与挣扎,成就了她的不凡,或许,也注定了她一生的孤独。
炒股配资10倍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长沙股票配资什么每日、每周、每两周
- 下一篇:西安股票配资平台陪伴不觉已过四载!值此